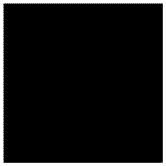按:本文為杜光宇於2014年9月及12月時,整理出的經驗與心得。
合作經濟的可能性
文/杜光宇
團體關係
最近有一本勞工自主企業的書,其實社運團體早就該實行這種方式了,唯一的差別是在這樣的團體裡面還是要有所區分,因為有些人是以一種合夥的心態進入的,那就是夥伴,對於夥伴的定義就是資源共享,包括以後生老病死都要一起扛在肩上,但同時對於這團體的付出也不能太計較個人,而必須以整個團體的利益為考量,另一種就是合作,也就是介於受雇者及夥伴之間,這可以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如果只是合作,當然團體比較重要的位置或資源就不可能放出來讓合作者參與,當然不管是合作或合夥都不能算是受雇者,所以這種情況這些人沒有老闆當然也沒有人能開除對方,唯一的差別只在於合作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進入合夥的關係承擔較重的義務,但同時也因此夥伴也必須保證不能讓合夥人陷於衣食無著因此在社運的路上難以為繼的窘境。
另一方面這種情況不表示團體就應該是剛性的或有很強的紀律性,這樣的團體就是在大方向上一致,在分工上如果可以以團體發展為重點那也就不會計較太多,但團體的每個人還是保有可以創造及開拓其他領域的自由性,在不影響團體分工的情況下,對於其團體外的關係其拓展還是尊重其意願發揮創意。
比合作更低的情況就是受雇,如果一個人的意願是如此,那就以受雇的方式處理,當然受雇者還是可以決定要上升到合作或者合夥的關係,這有其階序性。
合夥、合作、受雇,這是三個不同的階段與對團體發展方向向心力的程度差異,同時在一個團體裡這三個不同情況也有不同的責任義務規範或權力、權利等,我們在團體裡要搞清楚這樣的定位跟關係,否則就一直陷於彼此壓迫與錯誤的期待中,或者不斷發生明明不承擔責任與義務卻在團體裡要求與其他合夥人權力對等的情況
修正再修正
我們對於工會那種純粹的辦理團康、烤肉、自強活動跟發禮卷的福利路線是不同意的,但我們對於超出現在現實情況,強調鬥爭,造成只有少數工會菁英與工運組織者一廂情願熱衷的唯心及脫離基層的激進浪漫路線也是不同意的。
因此,我們才希望走上合作經濟的工會路線,我們才希望工會潛進工人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才希望工會不是只是停留在勞資爭議以及勞動權益。
重點是在這樣的基礎裡,我們才能往上成長工人的階級意識以及政治發展,而民主的溝通以及組織裡進行進步的政治教育才有可能!
但這樣的政治教育不是在課堂上的,它就是在工會踐行了對於會員生活負擔減輕的可見的具體成果上,才會具有它的可信力。
團體關係
最近有一本勞工自主企業的書,其實社運團體早就該實行這種方式了,唯一的差別是在這樣的團體裡面還是要有所區分,因為有些人是以一種合夥的心態進入的,那就是夥伴,對於夥伴的定義就是資源共享,包括以後生老病死都要一起扛在肩上,但同時對於這團體的付出也不能太計較個人,而必須以整個團體的利益為考量,另一種就是合作,也就是介於受雇者及夥伴之間,這可以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如果只是合作,當然團體比較重要的位置或資源就不可能放出來讓合作者參與,當然不管是合作或合夥都不能算是受雇者,所以這種情況這些人沒有老闆當然也沒有人能開除對方,唯一的差別只在於合作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進入合夥的關係承擔較重的義務,但同時也因此夥伴也必須保證不能讓合夥人陷於衣食無著因此在社運的路上難以為繼的窘境。
另一方面這種情況不表示團體就應該是剛性的或有很強的紀律性,這樣的團體就是在大方向上一致,在分工上如果可以以團體發展為重點那也就不會計較太多,但團體的每個人還是保有可以創造及開拓其他領域的自由性,在不影響團體分工的情況下,對於其團體外的關係其拓展還是尊重其意願發揮創意。
比合作更低的情況就是受雇,如果一個人的意願是如此,那就以受雇的方式處理,當然受雇者還是可以決定要上升到合作或者合夥的關係,這有其階序性。
合夥、合作、受雇,這是三個不同的階段與對團體發展方向向心力的程度差異,同時在一個團體裡這三個不同情況也有不同的責任義務規範或權力、權利等,我們在團體裡要搞清楚這樣的定位跟關係,否則就一直陷於彼此壓迫與錯誤的期待中,或者不斷發生明明不承擔責任與義務卻在團體裡要求與其他合夥人權力對等的情況
修正再修正
我們對於工會那種純粹的辦理團康、烤肉、自強活動跟發禮卷的福利路線是不同意的,但我們對於超出現在現實情況,強調鬥爭,造成只有少數工會菁英與工運組織者一廂情願熱衷的唯心及脫離基層的激進浪漫路線也是不同意的。
因此,我們才希望走上合作經濟的工會路線,我們才希望工會潛進工人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才希望工會不是只是停留在勞資爭議以及勞動權益。
重點是在這樣的基礎裡,我們才能往上成長工人的階級意識以及政治發展,而民主的溝通以及組織裡進行進步的政治教育才有可能!
但這樣的政治教育不是在課堂上的,它就是在工會踐行了對於會員生活負擔減輕的可見的具體成果上,才會具有它的可信力。